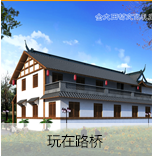推荐理由
《逝者如渡渡》如同生命的绝响,在一咏三叹中向几百年来因人类过度活动、捕杀迫害而整体覆灭的动物和人类少数族群作最后的道别。在书中,作者尽最大可能描摹他(它)们的样子,将每一种生命独有的美丽,与自然水乳交融的关系写得入木三分。深情忧伤的文字中,仿若窥见工业革命以前,一个充满善意、生机勃勃的世界。
最后一只渡渡鸟、最后一只旅鸽、最后一只隆鸟、最后一只异龙鲤……最后的最后,只能留下一个荒凉无望的世界。
全书充溢在哀伤的氛围之中,对美好生命的赞美与对无情杀戮的鞭挞交织在一起,再将人类族群与族群之间,人类与自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摆放在一起,不论是诘问、哀叹、还是反思,那些文字都令人不忍直视又欲罢不能。面对人类曾经对各种生灵的残忍迫害,我们尽管不是直接的杀手,却也难置身事外。在时空交错中,在回望与展望之间,没有人可以拒绝那些逝去生命留给地球最后的回响。文字无法为逝去的生命招魂,但起码它是对人类残存的良知、悲悯的记录,或许百年后,它是我们的孩子凭以想象过去、感知神奇的唯一载体,失去了动物伙伴,我们的孩子们便如同折翼的天使,再难以生出天马行空的想象。
我以为渡渡鸟只是一种传说,它活在《爱丽丝漫游仙境》中,“渡渡鸟坐下来,用一个指头撑着前额想了好长时间,就像照片中莎士比亚的那种姿态……”但到今天我才知道,渡渡鸟并非传说。这种神奇的大鸟儿,曾快乐安然地生活在毛里求斯的岛屿上,气定神闲无忧无虑。然而自1505年它们被人类首次发现后,不出200年便灭绝了,它们死于人类的贪婪无知,死于人类的口腹之欲。如今只有唯一的一只残存的渡渡鸟头,被孤独地摆在牛津大学自然博物馆中。“逝者如渡渡”成了一句西方民谚,用以比喻逝者不复归,其中的忧伤难以言尽。
假如不是与渡渡鸟习性相似的火鸡,拯救了那片因失去渡渡鸟而险些“忧伤”至死的卡尔瓦利亚树群,不知还有多少无辜的生命将陷入生死劫。大自然有自己的法则,很多并非人类智力所及。书中介绍,有科学家正在试图用现代科技复活渡渡鸟,只是我更担心它们复活后的命运,是进入现代养鸡场以备人食用?还是在动物园中成为拉动旅游经济的助推器?人类能还它们一片自由的生存空间吗?或许,不改变人类自身,这些动物即便复活,遭遇的也是生不如死的劫难。
几百年间,在地球上永久消逝的物种又何止渡渡鸟?在白令岛,曾经生活着一种神奇的“美人鱼”海牛,它们常常在黄昏的余晖中浮出海面,抱着孩子哺乳,披散在头上的长长海草使它们看上去神秘、高贵,就如同人类的远亲,但它们却在被人类发现的26年后,被刀削斧剁捕杀净尽。小小的倭狼、高大的隆鸟、长寿的象龟、神秘的白狼、不愿与人类合作忧伤的亚洲猎豹,自从它们生存的土地遭遇人类这种外来物种的入侵,它们的生命就走到了尽头,只留下一段段传说。
为这些逝去物种殉葬的当然还有人类自己,他们是毛利人、贝奥图克人、阿伊努人……以及已经叫不上名字孤岛上的土著民族。这些曾经在封闭的地区独自生活、独自繁衍的种族,他们曾经看上去那么强悍,它们能够在丛林间飞奔逐鹿、驾一叶轻舟称雄大海,拥有神秘的与自然和谐相生的能力。然而他们远离人类的纷争太久,面对外来“文明”人的野蛮入侵,毫无招架之力,用生命献祭、血染家园、被驱逐、被奴役成了他们难逃的命运。书中记述,很多地方土著民族已经遭遇灭顶之灾,没有留下最后的血脉,有些土著在屈辱中妥协,与外来入侵者渐渐实现了种族融合,他们的记忆正在消逝,曾经古老的生活方式消逝在了现代文明之中。
麋鹿传说,是全书中唯一一个不以悲剧结尾的故事。中国最后的18头麋鹿险些与大清王朝一同覆灭,偶然的机遇,它们被一位英国公爵购买,远渡重洋劫后重生,如今全世界近3000头麋鹿都是当年18个幸存儿的后代。镜头回到现代中国,一位人类妈妈救助了一头刚刚出生的小麋鹿,将其抚养长大并助其一波三折地回归鹿群。人类的一点善意,终于被麋鹿群体接纳,这让我们对自然不安、负疚的心有所舒缓,但这种个别的救助,相对于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动物群体而言,依然是杯水车薪。
一个动物种群的持续繁衍,需要的是大自然的庇护。保护自然的生态平衡,还各种物种在地球上自由生存权,需要强势的人类在欲望面前止步,然而对自然不予不夺,圈定自身行为的边界,恰是人类最难做到的。